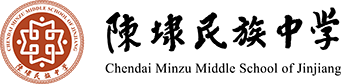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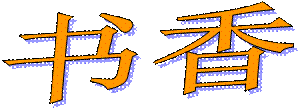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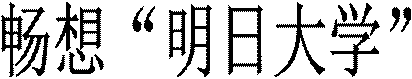
 毫不夸张地说,高等教育领域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会牵动公众的神经。从大学扩招到“双一流”高校建设,从毕业生就业去向到每年的大学排行榜,概莫能外。毕竟,在中国老百姓看来,大学是迈向成功人生的关键一步,十年寒窗苦,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因此对大学的关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在世界其他国家亦是如此,从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1809年在德国柏林创立至今,大学制度已经走过200多年的历史,面对互联网及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面对大数据、人口老龄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的挑战,很多有识之士也在思考,大学的明天将何去何从?对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近引进出版了美国未来学家戴维·斯特利(David J.Staley)的研究成果《重新构想大学》,他凭借对高等教育未来形态数十年的观察思考,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平台大学、微学院、人文智库、游学大学、博雅学院、接口大学、人体大学、高级游戏研究院、博识大学、未来大学等十种“明日大学”的模型,这对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工作者而言,或许就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毫不夸张地说,高等教育领域的每一次风吹草动,都会牵动公众的神经。从大学扩招到“双一流”高校建设,从毕业生就业去向到每年的大学排行榜,概莫能外。毕竟,在中国老百姓看来,大学是迈向成功人生的关键一步,十年寒窗苦,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进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因此对大学的关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在世界其他国家亦是如此,从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1809年在德国柏林创立至今,大学制度已经走过200多年的历史,面对互联网及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面对大数据、人口老龄化以及后疫情时代的挑战,很多有识之士也在思考,大学的明天将何去何从?对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近引进出版了美国未来学家戴维·斯特利(David J.Staley)的研究成果《重新构想大学》,他凭借对高等教育未来形态数十年的观察思考,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平台大学、微学院、人文智库、游学大学、博雅学院、接口大学、人体大学、高级游戏研究院、博识大学、未来大学等十种“明日大学”的模型,这对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工作者而言,或许就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把书作者戴维·斯特利称作“未来学家”应是名副其实,因为他在20年前就开始“认真、持续地开展预见未来的研究”。他的职场身份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历史学教授,出版过《头脑、心智与互联网的深度历史及未来》《历史与未来:以历史性思维想象未来》等著作。身为象牙塔中的一员,又以未来学研究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可以想见,他对大学教育的展望与前瞻,必定是怀揣梦想而又踌躇满志。读罢全书我有一个总体的感受,面对纷繁复杂的不确定因素,作者在研究态度上始终秉持一种谨慎的自信。
这份自信多半源自若干年前由“慕课”(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引发的一场大讨论。早在1997年,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就宣称:“30年内,庞大的校园即将作古。大学将无法生存。这是一个与我们第一次获得印刷书籍时一样巨大的变化。”种种迹象表明,一场颠覆美国高等教育的“超级大地震”即将到来,以至于当慕课引领的在线教育快速崛起之时,很多大学的管理层显得惊慌失措,不得不仓促应对。而就在舆情一边倒的时候,斯特利的独立思考能力帮助他成为了公共讨论中的逆行者。他在演讲中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慕课不是“超级大地震”,让顶尖大学通过慕课来免费提供所有课程的想法,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后的事实映证了他的判断,慕课在爆红之后很快归于平静,营利性组织根本无法颠覆高等教育,传统校园行将崩溃的预言彻底落空。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次品尝到胜利果实,也让斯特利对于高等教育创新的研究信心倍增。
与此同时,身为历史学教授的斯特利,始终抱持一种严谨而谦逊的态度,谦称书中推出的十种明日大学形态,是“可行的乌托邦”,即它们虽是想象的产物,但不是凭空想象,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实现的潜力,但是,即便目标实现也并不意味着找到了尽善尽美的方案或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乌托邦也需要与时俱进进行自我革新。在他看来,“大学的问题不是缺乏创新,而是缺乏关于创新本质的想象力”。因此,讨论明日大学何去何从的关键就在于,必须专注于创新带来的转型体验,跳出“我向你付费,你帮我证明技能”的传统思维,更广泛、更有想象力地寻找潜在的创新来源。于是,斯特利效仿运用推测性设计制造“概念车”的成功案例,用十种“概念大学”来描画心中的蓝图。
在这部书中,十种“概念大学”被归入四个板块,分别是“组织”“学制”“技术”和“属性”,这正是斯特利运用发散性思维憧憬未来高等教育创新的四个维度。比如,“属性”板块,顾名思义,是从大学教育的根本属性层面推陈出新,通过聚焦培养特定类型的毕业生来重新设计大学的运作模式。隶属这一板块的三种全新的大学形态个个拥有“独门秘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高级游戏研究院,光听这校名就足以颠覆很多人的传统观念,该研究院将“游戏即目的”作为自己的院训,致力于培养资深游戏玩家的想象力。博识大学,这里的学生必须主修一门科学学科、一门人文艺术学科以及一门职业学科,这样的跨界设计可谓用心良苦,因为创造力和创新思维通常会在这些不同学科的交汇处产生。第三种则直接被命名为“未来大学”,该校学生置身于一个一个具象化的未来场景中,课程分为纯未来学和应用未来学,可以说,从理论到实践,就是要培养一批懂得设计未来的学生。

 作家在书里、书外都一再声明,《笑的风》或可改题为“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虽然这与普希金的著名诗作同题,我觉得内涵却大有差别。普氏生活的时代、地域、环境及其个人生活遭遇,当然无法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我国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时期,经历过疾风暴雨、惊涛骇浪、大起大落的考验,也感受过相对民主自由、和平稳定、团结和睦的气氛,享受了改革开放、繁荣发展的成果,而且耄耋之年依然初心不变、心态平和、身心健康的王蒙先生相比。更重要的是,王蒙在小说中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理解、反映、评述,与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是迥然不同的。
作家在书里、书外都一再声明,《笑的风》或可改题为“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虽然这与普希金的著名诗作同题,我觉得内涵却大有差别。普氏生活的时代、地域、环境及其个人生活遭遇,当然无法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我国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时期,经历过疾风暴雨、惊涛骇浪、大起大落的考验,也感受过相对民主自由、和平稳定、团结和睦的气氛,享受了改革开放、繁荣发展的成果,而且耄耋之年依然初心不变、心态平和、身心健康的王蒙先生相比。更重要的是,王蒙在小说中对现实生活的感受、理解、反映、评述,与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是迥然不同的。
20世纪末,在我国小说界自70年代后期开始相继出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基础上,文学理论家们提出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概念,提出作家不仅要关注、热爱生活,而且应该站在社会时代的高度看取社会走势,把握时代脉向,同时将自己的审美激情灌注到作品形象中去,给人们以感染和鼓舞,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认为现实主义精神不仅要求作品真实地再现现实,而且要求“以热情为元素”,展现生活的愿望和理想。我以为,这种“新现实主义”其实就是注入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复合体,似乎缺失了“关注、热爱生活”的最坚实的基础,即作家对现实社会生活长期切身、深入、透彻的体验和感悟,对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把握与评判,对最广大民众精神与物质生活需求的了解与探索。即如王蒙在《对话》中所明言的是“接地气”“要通气”:“我努力去接农村的地气,大城市的牛气,还有全世界的大气、洋气、怪气,更要让这些材料通气:通上新时代、新时期、历史机遇、飞跃发展、全面小康、创业维艰、焕然一新、现代乃至后现代的种种。”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王蒙“运用了年事高者的全部优势,各种记忆、经验、信息、感慨,全来了”。在《笑的风》中,几个主人公傅大成、白甜美、杜小鹃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心路历程,他们的喜怒哀乐、起落成败、优点特点缺点弱点,都是作家熟知熟悉,且能以己解他(她),融合了我你他第一、二、三人称,融汇了感触、感喟、感叹、感想,也融进了作家自己的议论、评论和结论,做到了以小见大、以中国见世界的扩展效应。我起初读《笑的风》时,与单女士同感,觉得作家“有显摆之嫌”,但后来看到作家强调“生活的符号、历史的符号令我怀念,钟情无限。这比显摆不显摆重要一百倍”,改变了我的认识。
可见作品的时代特色鲜明,个人感悟突出,写作导向十分明确,诚如作家所言:“写不出大时间、大空间、大变化的小说,怎么对得起吾国吾民?”作家创作的欲望、动机、主旨、目的清晰明了,其中隐含了太多的感念、意念、忆念、思念,当然还有难以忘怀的怀恋、追恋、眷恋……于是,我想用另一个词“秀”来替代“显摆”——知识秀、辞语秀(包括书中排比句及外语的运用和诗词创作)、中外人物秀,最核心的是经历、阅历、资历秀,充盈全书。“秀”的本义是扎根于土地的谷类作物抽穗开花,引申为清秀、灵秀、娟秀、俊秀、隽秀、秀丽、秀美、秀伟等等,当然都是褒义词(与贬义的动宾词组“作秀”异意)。近期,我有幸随同王蒙先生再次回到新疆调研。在这片他曾经生活和工作了16年的广袤而多彩多情的土地上,他每到一处,都充满了与各族民众旧雨新知欢聚的动人场景和热烈气氛,也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位“接地气”的人民艺术家回到“第二故乡”的轰动效应。作家“接地气”,就有了“人气”。对于王蒙先生60多年的文艺创作实践来讲,从北京到新疆,就是在和各族干部、群众的融洽相处中,不断汲取获取采取创作源泉、动力、素材,激发灵感,汇聚智慧,驰骋联想,就有了底气、勇气、名气、神气、牛气,汇聚成出色的“文气”,创作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欢迎所理解所赞赏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