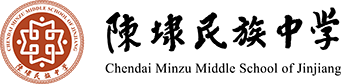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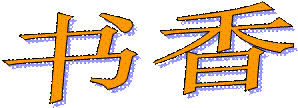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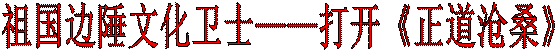
传记体长篇小说《正道沧桑》终于出版了。这是新疆一部用血泪传播、捍卫鲁迅文学和精神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塔依尔・拜合提,其生活原型是新疆鲁迅研究学会原会长,著名的维吾尔族翻译家托乎提・巴克。他生长于新疆喀什地区的一个偏僻贫困的村庄,在新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引领下,走上了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道路。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岁月里,他知道了十月革命、抗日战争、高尔基,并第一次听到了鲁迅这个名字。
作为一名维吾尔族人,他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学习汉语,崇尚中原文化,深受国学影响;在国民党的监状里,他偶得鲁迅先生的杂文集《热风》,被其中高扬“五四”精神、高举民主科学旗帜、彻底反帝反封建、反国粹主义、扫除迷信落后、主张社会解放的思想內容所震震撼和鼓舞。从此,他开始崇敬鲁迅,热爱鲁迅,苦学汉语,广泛收集研读鲁迅作品。
鲁迅先生的文学思想深刻地感染和熏陶了他,鲁迅先生硬骨头的革命精神以及蔑视奴颜媚骨的高尚人格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他,鲁迅的文学思想及坚强性格成为他生命的灯塔,照亮了他一生苦难的命运历程,使他坚定不移、无怨无悔地终生追随鲁迅。鲁迅的作品博大精深,其中有些作品艰深难懂。为了能精准地翻译鲁迅文学及思想,用最恰当的维吾尔族语言表现鲁迅作品的独特风骨,他刻苦研读鲁迅作品,深入领会其思想精髓,认真揣摩其作品独有的风格和韵味。他博览群书,精学中外历史、哲学和文学,为翻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终于完成了500多万字《鲁迅全集》的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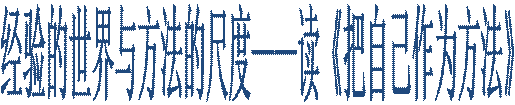
于一般读者而言,阅读这本书没有多大的知识性障碍,也不需要系统的知识储备,但它很大程度上的意义是想象力的边界再度被打破或被确证,就像作者项飙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所说的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乡绅的传统。在这样个相对熟悉且自恰的世界中,乡绅的伦理判断既不同于调查员的客观中立,也与人类学学者的细节剖析、结构呈现与意义生产迥然不同。它可能是一个存在鲜明边界且带有明确痕迹的历史“叙述”或者现实“图景”。当然,也可能是对现存刻板印象的超越,在一个严密或模糊的系统里找到缝隙看清内在的“文化传统”。用另外一位对谈者吴琦的话说,这本书无疑是“在无声处听见有声,在边缘处发现边缘”。它以“谈话作为载体,人类学作为中介,乡绅作为思想资源,自我作为方法”,由此而构筑清晰的思想脉络,提供给读者的是一次自我检视的尝试,并“以此找到观察和反思的位置”。
作为经验的世界全球化与地方性,必须承认,项飙从某种意义上是经验的集合体,而经验的开始则来自于家庭,来自于温州,来自于从小的教育。他是一个被知识分子式的生活传统、阅读传统和教育传统构筑而成的人,如同他所述,可能外祖父和舅舅们对他的影响是带有某种先验性的,也正是这种不同层级世界的经验混杂和话语杂糅带给他对现实的思考始终伴随着一种“自洽的距离感与直接性”和“话语阐释的差异性与多维度”,并且能够在不同的位置中保持和谐的自恰。
作为方法的尺度,人类学的观察视角重新发现人类学,或者说发现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项飙在2020年给我们的一个巨大启示。如何在捉摸不定的社会科学中采用一种相对量化或者具有实证性的方法对当前一些难以判定的社会现象或者历史图景,在一个有距离感的观察位置上,给出一个相对确信的答案。当然,这同样是项飙作为人类学家将经验和方法熔铸在具体问题当中的某种正当性策略。无论是《十三邀》节目中探讨的“附近的消失”还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项飙谈到的作为学术“图景”描绘的重要性,那种不带价值判断和不以臆测、揣度为基准的认知行为,都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