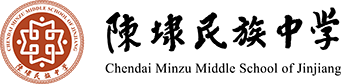|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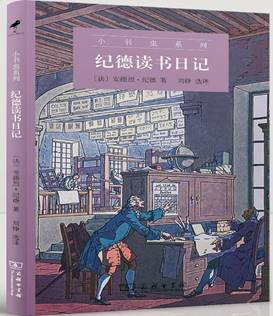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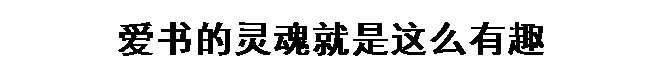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这是宋代诗人翁森在《四时读书乐》中描绘的意境。另有一首美国作家吉恩·福勒的诗是这样写的:“因为书籍不仅是书籍,它们是生活/是过去时代的中心/是人们工作、生与死的原因/是他们生命的本质与精髓。”这两首诗都可视作对书籍一往情深的告白。不知诸君读后是引为同道、无动于衷、莫名其妙、嗤之以鼻,还是不以为然?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有这样一群人,书痴、书虫、书蠹、书迷、藏书家、猎书人,这一系列称谓都是在为他们画像,书在他们眼中绝不仅仅是一件印刷品,对他们来说,拥有一本心爱之书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得不说,爱书人的存在将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有趣、温暖。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这是宋代诗人翁森在《四时读书乐》中描绘的意境。另有一首美国作家吉恩·福勒的诗是这样写的:“因为书籍不仅是书籍,它们是生活/是过去时代的中心/是人们工作、生与死的原因/是他们生命的本质与精髓。”这两首诗都可视作对书籍一往情深的告白。不知诸君读后是引为同道、无动于衷、莫名其妙、嗤之以鼻,还是不以为然?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有这样一群人,书痴、书虫、书蠹、书迷、藏书家、猎书人,这一系列称谓都是在为他们画像,书在他们眼中绝不仅仅是一件印刷品,对他们来说,拥有一本心爱之书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得不说,爱书人的存在将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有趣、温暖。
人类文明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作家、学者,是我能想到的最纯粹的爱书人,而且个个阅读量惊人。比如,法国大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他82年的生命长河中,读书几乎是每一天必做的功课,《纪德读书日记》(商务印书馆出版)就是从他60年的日记中选译与读书相关的内容汇编而成。对书籍发自内心的挚爱散布在日记中,随处可见,读者首先会惊叹于他的阅读范围极其宽广,不仅有《鲁宾逊漂流记》《约翰·克利斯朵夫》《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文学作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他甚至从头到尾读了三次,每首诗连续读两遍,而且包括宗教、哲学、科学等多方面的书籍都在他的涉猎范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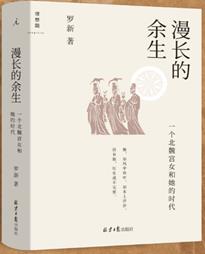 传统的历史书写,记述的常常只是“帝王将相们的故事”,绝大部分不能入史的小人物可说是“没有历史的人”。帝王将相终究遥远,缺少了理解之同情,史书阅读往往枯燥且无趣。
传统的历史书写,记述的常常只是“帝王将相们的故事”,绝大部分不能入史的小人物可说是“没有历史的人”。帝王将相终究遥远,缺少了理解之同情,史书阅读往往枯燥且无趣。
中国现代史学之父梁启超曾断言中国无史:“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00多年过去了,梁启超对近世史家的期望渐成现实。现代历史学者开始下移目光,关注那些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的经历,挖掘一段微观史,讲述“没有历史的人”在历史中如何生活。由此,一些历史的幽暗角落被重新照亮,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2022年7月,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和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
2022年7月,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和鲁西奇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
王钟儿生长于南朝刘宋的中下层官僚家庭,出嫁没几年,因为一场边境战争,30岁之际被掳掠北上,被送到北魏首都平城宫中做宫女。此后她“历奉五朝,崇重三帝”,活了整整86岁,完整地见证了那个时代。喜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的主人。他生在秦始皇时代,比秦始皇嬴政大三岁,死于始皇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之后四年,比秦始皇早死七年,终年46岁。他们能够被今天的我们所了解,除了得益于考古发掘,还依赖于两位历史学者的历史自觉与书写视角的切换。王钟儿和喜相距遥远时空,却如此相似,这不是偶然的。在权力世界里,他们所能拥有的选择很少,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权力本身。经由他们,我们更能体会历史的残酷。两位作者把零星的材料串连起来,尽可能讲述主人公的一生,站在他们的生活里,去呈现那个时代的风貌,比如通过喜的从军、为吏等经历,解读了秦制的精细度与控制力。因此,细读完两书,与其说了解了两个卑微个体生命的面相,不如说知晓了他们时代的权力运行真相。